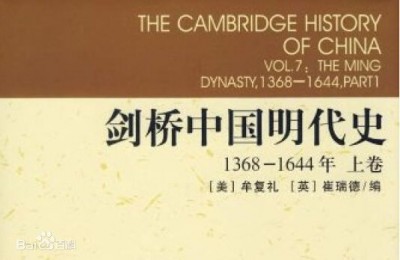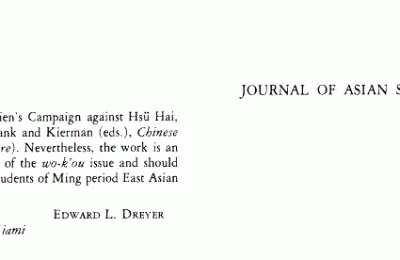这篇文章主要是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对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作用。
在讨论之前,得先说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这个问题。兹引一位研究近现代中国史学史的土耳其裔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所论作为引言:
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社会历史学者的谜,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中国为什么从未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人们想要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动力,也与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有关。此外,在他们试图发掘中国历史中的资本主义的努力中,中国历史学家发掘出的史料,大幅度地改变了曾经流行一时的中国经济停滞论。的确,近年来相关的学术著作显示,帝制时代晚期中国社会出现了持续渐进的商品化。
一、中国社会史论战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的起源
鸦片战争以来的失败,使得中国的学者都在思考近代中国为什么会衰弱、会落后,检讨它的病因,希望找出解决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注意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作用。西方帝国主义者对他们的侵略有一套说法,尤其是19世纪的“新帝国主义”者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尤其像中国社会,是长期停滞的,靠其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决;西方帝国主义者也说他们带来的新科技和资本帮助中国把停滞的社会生产力激活了,故他们不是侵略者,而是教育者。这种说法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袭用,他们在侵略中国的时候,就说“皇军”是来给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力量予以最后的打击,这样中国社会才可以从长期停滞中解放出来。
这种说法当然使得中国学者非常不满。大家开始研究中国社会有没有长期停滞?如果停滞,是为什么?在这个检讨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次重要的讨论,也就是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北伐革命军分裂,共产党遭受了相当大的打击,当时认为这是革命的失败,于是一起来讨论中国革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大家认为中国革命出问题是因为参加革命的人没能正确理解当前社会的性质、当前的社会问题和当前社会的形态,因此发动了错误的革命。当时不论左、右派,所用的理论和词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都认为中国跟世界各国发展的进程是一样的,都是先有原始社会,然后发展到奴隶社会,再发展到封建社会,然后在封建社会晚期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萌芽不断壮大,就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有了资本主义以后,资本主义的腐败和错误就会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再进一步发展,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如何来判定现代社会的性质,就要注意到现代社会之前的社会。于是就进一步讨论近现代之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及其性质。这个讨论并不成功,因为参加讨论的人基本上是“以论代史”,且多采用选精和集粹法,所用的证据和史实并不充分,只采用跟其相符、能支持其实证的史料。在这种情况下,就各说各话,没有交集,没有真正的讨论。但在讨论中还是找到一些过去少人知道的史料和史事,像吕振羽和邓拓,就根据这些材料说中国在封建社会晚期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讲法,后来被毛泽东写进《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句经常被用到的名言:“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就是说,中国在封建社会晚期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力干预,中国也会缓慢地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因而,这个讨论就证明了中国近代以前的社会,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不是停滞的社会。但这个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就成为大家要问的问题,这正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的起源。
二、“五朵金花”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必然性,要从历史发展来予以说明,于是有5个被称为“五朵金花”的历史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被提了出来。
吕振羽和邓拓只是简单地提出资本主义萌芽,讲得并不是很清楚,用的文字也不多。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包括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分期,以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两大问题。
中国古代史就是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怎么来分期,分期基本上是证明人类社会五段发展论的正确性。后来衍生出近现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也就是从战国时代到清前期中国的土地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的问题。
古代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里面农民问题最重要,而农民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所有制。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经常产生“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土地兼并现象。地主就成为支配阶级,他们在社会与政治上都占重要地位。
第三个问题是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
在朝代的末期或中期,经常发生社会政治危机,受迫害的农民于是起来反抗。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虽然农民战争大多失败,少数成功的也未建立农民政权,而是向封建政权蜕变,但农民战争还是教训了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也必须向农民让步,因而仍然能推动历史前进。因此农民战争不能视为流寇之乱,要把过去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第四个问题是汉民族的形成问题。
主要讨论汉民族形成的时限,究竟是秦汉之际、明代后期、清代还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汉族是其中最大的部分,所以要阐述这个多民族国家,就必须讨论汉民族是怎么形成的。汉民族本身就是由多民族构成的,讨论民族形成问题就是要理解多元的概念,才可避免单一或多数民族的沙文主义。1949年以前,翦伯赞就批判“大汉沙文主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孙中山开始,就讲国内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所有的民族在大中华里面都有一个重要的地位,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其主要贡献。虽然在持续时间及成果数量上,与其他四朵“金花”相比,汉民族形成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昙花一现,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直到现在,历史文化认同、多民族统一发展、国家及民族起源等重大理论问题日益成为热点,其学术意义影响深远。
最后一个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前近代中国社会是不是停滞的。长期以来,西方的讲法是,比较马可·波罗的游记和清末传教士们所叙述的中国社会情况,就发现中国没变。这个讲法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来的,他说:“中国似乎长期停滞不发展了。五百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曾对它的耕作、制造业以及众多的人口作过详尽的描述,然而它们与今天到过中国的旅游者的描述还几乎相同。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之前,中国的财富就已经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许可达到的程度。”依此说法,从马可·波罗时代一直到近代乃至现代,中国的经济几百年来一直都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要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人自己是办不到的,只有靠外来力量,引进外来资本和新科学技术,才能解救这个发展停滞的古老国家。照这个说法,停滞的中国当然产生不了资本主义萌芽,更不要说构成近代文化主要成分的资本主义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主要在辨明历史上的中国是否能自力发展出资本主义。如果能,就表示中国自力更生,不靠外力,也能近代化;如果有困难,困难出在哪里,该如何解决。这对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是古为今用的史学任务。
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就是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具有过渡性和双重性。
要谈资本主义萌芽,就要先说资本主义萌芽到底是什么,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来自吴承明:这个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对于它所出现的社会跟时代来说,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是有延续性的。要判定封建社会晚期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就要讨论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到底是不是农奴性的,工匠的身份是否受地主或作坊主人控制,有没有自由雇佣,也就是他有没有自由选择主人的权利。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雇佣关系上。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明清时代,但许多研究明清以前的古代史学家也参与讨论,出现的论文相当多。中国人民大学把讨论中的重要文章收集起来,出版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在论文集“编者的话”里面,不但说明了讨论的学术任务和意义,并且指出这个讨论的政治任务:“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中国比较科学地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且有助于我们把中国历史从特殊论、循环论等的唯心主义泥坑中解救出来”。所谓“特殊论”,就是中国跟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就像说有一种什么先进的东西到中国来是不适合的,因为中国有特殊的国情。所谓“循环论”,就是说中国历史发展模式是循环的。这些都是唯心主义的讲法。
20世纪50年代的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不但有助于把中国从唯心主义的泥坑里面解救出来,还能“有力地驳斥帝国主义污蔑我国社会只有外力侵入才有进步和发展的胡说”。这也证明了毛泽东所说的那段话的正确性,即“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也就是说,由于资本主义是罪恶的,是对人民不好的,所以中国要发展出进步的社会主义来解救它。可是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的过程,封建社会晚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新生事物,是进步的。而且,相对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退步的,是不好的;但相对于封建社会来讲,资本主义萌芽却是进步的。所以,中国如果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说,中国的DNA里面有了自己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因子,是自发的力量,不是引进的,那么资本主义就不必从外面引进来,中国自己可以发展出来,即使是“缓慢”的。
后来大量的研究就讨论到,为什么中国没能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成资本主义,要等到近代西方帝国主义者来了以后才使封建社会完全解体。对此的解释是,有两个力量阻碍或迟缓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一个是外力的帝国主义入侵,把正在发展的历史进程打乱了;另一个就是内部敌人,封建地主阶级扯了发展的后腿。因此,中国要发展就得对付这两个力量,要反帝反封建,中国才可以挣脱这些束缚,继续向前发展。这就是中国社会史论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任务。
四、西方学者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的关注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受到美国和苏联史学家的关注,他们认为这是了解中国政治的途径之一。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出版后不久,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头人费正清的学生费维恺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述中国学界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另外《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还在1964年主办了为期7天的“中共史学研讨会”(Conferenceo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iography),评论包括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内的中共新史学,其结论为大多数西方学者所认同。
西方史家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基本看法是传统中国社会并未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他们认为中国史学家之所以主张封建社会晚期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是要证明中国人自己有能力推动社会的进步,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站起来。这背后是从中国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要放在这个脉络中来看。费维恺引用当时苏联史家对中国史家的批判,说:中共史家采取“教条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的批评也传进大陆。大陆史家受到挑战,不少人开始反省这一长久被接受的明清社会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甚至开始怀疑这种说法。慢慢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开始从历史研究的主要舞台退场了。
在这个过程中,李伯重先后发表《“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两篇文章,反省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讨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他指出:“我们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可能只是我们强烈地希望如此,而不一定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而言,我们对萌芽的信念,也就只是一种情结。……无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解释有多大的分歧,它毕竟指的是最早状态的资本主义。不清楚资本主义是什么,当然也就无从谈论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然而,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今日,在国际学坛上仍然是一个聚讼甚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大陆史学界本来对资本主义萌芽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尚钺几乎是说到了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很壮大。如果是这样,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就具有近代性,有了近代性因素的社会,就应该是近代史的开始。这与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讲法就不一样了。尚钺的讲法遭来很多批判。这种讲法,应该就是李伯重所说的“强烈地希望”。
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常常因为我们的强烈希望而改变或是主导了我们的结论。李伯重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史家反省和检讨。历史研究必须要求真,求真就要客观,情结会破坏客观性,会影响结论的正确性。研究历史要求真,也要求用,但真的东西才有用,不能求得客观真相,得到的就会是假结论。拿假的结论去用,就会有偏差,就会有错误。所以对这个情结必须要反省。
这里要补充讲一下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西方国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关注,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东南亚局势,都说明当时中国非常支持东南亚的社会主义革命,支持反帝运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认为他们最大的敌人,一个是苏联,另一个就是中国。美国为掌握世界霸权,就必须了解他的敌人,因此他们很注重苏联研究和中国研究。1958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个《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鼓励资本家来资助各大学的第三世界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于是许多基金会拨款资助中国研究,尤以福特基金会出钱最多。在他们的资助下,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华盛顿、匹兹堡等23所著名大学成立了东亚(以中国为主体)研究机构。已有中国研究与教学机构的大学,如哈佛、芝加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也接受资助,培养“中国通”。培养大量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人,就是要作为他们的情报工作或是商业发展的参考。这类研究人员的来源就是各大学的东亚系。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送了大批博士研究生到中国台湾学中文、做研究。他们很多人研究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但也有不少人研究中国古代史。
上面提到苏联史学家说中共史学家采用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于这个论点,美国史学家也表赞同,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他们认为中国史家的研究是为希望重新站起来的中国政治服务的,是民族主义的,因此不客观。对一些有争论的议题,他们与中国学者讨论到不大能够招架的时候,就会说中国学者是不可救药的民族主义者,其历史研究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其实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的研究,跟他们成立的中国研究和教学机构一样,并没那么纯粹。在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时,不能盲目附和西方学者的说法,要实事求是地探究。只有理清这个讨论的发展过程,把它搞清楚,才能进一步来理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
五、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
(一)第一个阶段:20世纪30至40年代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第一个阶段,是“社会史论战”之后的20世纪30至40年代。除了吕振羽和邓拓以外,还有一位重要的史学家——傅衣凌。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的傅衣凌,原任职于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抗战期间,随省政府迁到永安,他在永安一个村子的阁楼里找到了一箱从明代后期一直到近代的地契、契约文书,利用这些契约文书写了《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不但讨论土地所有制,而且指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就是社会经济史研究,强调不能只靠《食货志》这一类的官书,必须注重民间文献。现在非常流行的做历史研究就要到历史现场做田野调查、口述历史,去找遗留在民间社会的史料,如碑文、墓志铭、家谱、账本等,均是傅先生首倡的。
傅先生曾说过一段话,说明了“社会史论战”的影响。他说:“我踏进大学之门时,初是念经济系的,嗣又想进国学系,后才转到历史系来的。因而在选修和自学的过程中,不仅修习本系的课程,还大量选修社会学系、国学系以及经济系的课程。……刚好那时国内正在掀起社会史论战,我们几个同学对这次论战都十分感兴趣。在这次论战中,我开始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不用说,那是极初步的点滴知识),尤其对社会发展诸形态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最喜谈论,并时时和同学邓拓、陈啸江等人交换意见。”
当时,这些青年学者开始探讨“社会史论战”引发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批判需要靠外力才能打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谬说,尤其反对日本所谓“皇军武力”会“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的说法。于是他们在明清社会经济史料中寻找手工业与商业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与生产关系”的萌芽,来证明在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前,中国社会经济不是停滞的,而是已经出现重要的变化。这就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个问题讨论的起源。
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首次提出明末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认为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反映了“萌芽状态中的市民思想”,“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940年,吕振羽更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一文中,具体指出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在明清之际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之后,在《简明中国通史》(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版)中特立一章“由封建经济的复兴到崩溃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进一步论述。
邓拓在《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一文中提到:“在西方列强侵入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内,已经存在和发展着否定它的母体的因素了。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由其自体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是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截断了这一历史的阶段,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傅衣凌说:“一九五四年一月我写了《明代苏州织工、江西陶工反封建斗争史料类辑——附论手工业劳动者在农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同年九月,我又发表了《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我在文中提出江浙的纺织业已向工场手工业发展,出现接近资本主义家内作业的最初生产形态,虽然新出现的东西尚非完备,而只是片断的、偶然的散在,但这种新的力量却逐渐孕育滋长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也发现明代江南地主经济,在跟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已初步显现出新的经济成分,逐渐排除封建劳役制的束缚,而向资本制的过渡阶段的道路前进。那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史学界还很少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明清经济现象的叙述与分析几乎还是一个空白,因此,我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侯外庐、尚钺、陈振汉、杨开道等先生都有来信商榷。日本的天野元之助教授等也向我索取文章。第二年,关于《红楼梦》时代背景讨论后,许多文章才接触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二)第二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最初研讨的重点是关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与资本主义萌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加强民族自信心,抵抗美帝的围堵,强调传统中国即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没有外力的帮助,仍然可以自力更生,发展出具有近代性的资本主义,虽然脚步可能缓慢一点。因此,要证明和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出现在什么时代。有很多学者主张是明清,也有学者主张是唐代,有人主张宋代,有人主张元代,甚至有人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怎样来评价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和水平呢?
对于明末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有没有变化,学者们提出了不同观点,有人主张是有质的变化,也有人主张只有量的变化。如果是质的变化,则资本主义的萌芽已茁壮成长,于是就有人提倡近代中国应起于明清之际。黎澍为此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予以驳斥。另外,资本主义萌芽对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有没有影响?明清是否出现过市民社会和市民运动?这些问题也引发许多讨论,有人引用明代史籍中出现的“市民”二字的史料,来肯定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使社会产生布尔乔亚的“市民”阶级,明末城市发生市民暴动,有资产阶级市民运动的性质。但王毓铨解读这个史料的时候,发现“市民”是指“市居之民”,而非欧洲“civics”的译词;把明末“市民”比作欧洲中世纪末期的新兴资产阶级,把万历年间“市民”反矿监、税使的斗争称之为“市民运动”,是不对的。况且根据刘志琴的研究,万历民变主要是官员士大夫领导的,不是由新兴工商业主要人物领导的。所以,王毓铨说:“今人称反矿税监斗争为新兴资产者阶级的‘市民运动’,难免有将古代中国近代化,把中国欧洲化之嫌。”
还有一个要比较深入探讨的问题是,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仅要讨论纺织业、棉织业和丝织业,也要讨论矿冶业、制陶业、制瓷业、造纸业、榨油业、制糖业、盐业等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过程中,学者们从明清文集、地方志、小说、笔记、族谱等各种史料中爬梳、发掘出明清社会经济相关的史料,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尤其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史料。
六、殊途同归的中日学者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
今天我们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理解,很多得益于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者的成果。这不只是中国学者,日本学者的影响也很大。日本学者过去多被军部给予重大的任务,为他们的侵华服务,如秋沢修二就在1939年出版的书中说道:“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就是停滞、循环和倒退,只有依赖‘皇军的武力’,才能彻底打破这种局面,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研究盐业的佐伯富被派到江浙调查盐业和私盐。酒井忠夫研究民间信仰和民间组织,被派来调查帮会。二次大战战败之后,日本学者反省侵华战争,认为他们过去的研究都注重中国历史里面负面的东西,尤其注重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经验,叫做“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专门研究少数的非汉族如何统治大多数的汉族的经验,以此作为他们侵略中国、占领中国和统治中国的参考,但是这么做是错的。植村清二说:“中日战争对中国人力和物力予以不可估量巨大的损害,没想到六亿中国民众经此强力打击,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结集强烈的民族意识。中国就像一大块脆弱的生铁,经大战的灼热熔解,千锤百炼,锻炼成富弹性坚硬的钢铁。”
过去日本学者只注重研究中国历史的负面,现在要改从正面看了。西嶋定生首先研究江南农村手工业的棉纺织业,产业革命的发生与纺织业有关系,珍妮纺纱机一次可以纺2根纱,他发现明清太仓式的纺纱机一次可以纺4根纱。而且中国的纺织业早就用水力纺麻。虽然这不足以证明中国手工业在明代具备产生产业革命的条件,但至少可以说中国的手工业技术在当时是领先的。许多日本学者接着从事明清农村与城镇手工业及商业的研究,他们也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想从纺织业、矿业、盐业、陶业等方面研究明清手工业中是否出现“手工工场(Manufacture)”,讨论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商业资本进入农村与城镇手工业部门产生的“问屋制前贷生产(putting-out system)”。日本学者说的“问屋制前贷生产”就是“包买制”,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叫“散作制”;产业革命的生产方式是把工人集中在同一个厂房里面工作的工厂制,产业革命之前,东方西方都一样,是工人分散在个别作坊或在家庭工作的手工工场散作制。
因此可以说: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地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对前近代的中国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达成一些共识。这就促成了1957年翦伯赞率团访问日本,与日本学界就明清社会经济史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展开对谈研讨,双方的论文后来由铃木俊与西嶋定生编辑出版(『中国史の时代区分』東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成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5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代表作有: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史教研室选编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后来,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选编出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选录了1958年以后发表的论文。在1957年以前的讨论中,学者们的态度是比较严肃的,但其后的论文夹杂一些非学术的因素,甚至上纲上线的越来越多,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近代现代史组批判尚钺说:
要像尚钺同志的看法,清朝大土地所有制已经都是经营地主,资本主义关系已深入农村,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隶属关系已为契约关系所代替。既然三百年前资本主义已在农业中占领了如此雄厚的阵地,那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封建土地革命。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中收录了不少类似的论文,编排方式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很不一样,几乎每篇文章一开头就引经典作家、革命领袖的话,然后才展开论述,论述都在为经典作家的话作注疏,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不再是1957年以前那种实证为主的历史论述,走向“以论代史”为主的政治批判。因此,20世纪60年代的讨论就很难有新的发展。接着便发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停顿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没有进展。
七、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发展与反省
在困难之中,还是有不少学者暗中进行研究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初期突然出现大量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著的原因。
基本上,这时期出版的论著大部分还是秉承1957年以前那种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各部门的实证研究的传统,讨论的问题和结论也跟以前差不太多。大概还是找寻更多新史料来论述明清手工业和商业各部门的实况,并且讨论为何资本主义萌芽不能茁壮成长为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之初,中美于1978年底宣布建交,两国的学术交流也因此展开。最初由费孝通率领一批中国学者去美国访问,那时我在哈佛大学进修,亲睹他们的访问交流。访美的中国学者中历史学者只有李新,他当时主持《中华民国史》的编撰,接待他的是孔飞力。李新到孔飞力的研究班上,和学生讨论交流。当时的学生中有几位后来成为了知名学者,如印度籍的杜赞奇、华裔王国斌。接着美国学者也组团到中国来,介绍美国学者的历史研究,把所有有代表性的学者所写的文章都翻译成中文,方便交流。因为改革开放,西方史学方法与理论传进来了,某些禁区开始有了突破,不再纠缠于概念的争论,大家提出很多新的思想、新的问题、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真可谓百花齐放。史学研究的新发展有两方面:第一是较多地进行中西比较,主要是中国跟西欧的比较;第二是扩大史料的运用范围。在中西比较上,成果不是太好,主要原因是中国对西欧的历史了解不够,所以有些研究比较有问题,但总算是把自己的研究视野打开了。另一方面,实证研究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接续20世纪50年代傅衣凌注重民间文献研究的传统,改革开放时期的史学研究特别注意契约、文书、碑刻、档案等的搜集与运用,并且开始注重实地调查与口述历史。这恰好与从西方引进的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相契合。中国史学传统与外来新理论与方法的合流,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例如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新四史”运动,注重村史、家史、公社史、厂矿史,鼓励学者到民间去做调查研究,对较少文字史料的工人、农民作口述历史访谈,重建他们的历史。这个传统也跟西方引进来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恢复了当年费孝通他们所做的农村社会调查方法。
这一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吸引了许多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壮年学者,开始运用新方法和理论研究社会史和文化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范式,不再像以前一样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明显降温。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相关的论文越来越少,专门的论著出版也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反思。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结为“情结论”“死结论”“假问题论”等,如前面讲过李伯重的情结论,也有人说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根本是个假问题。甚至吴承明也以市场经济论明清社会经济,他讨论明清经济主要谈市场经济,谈全国市场。这给人的一个印象就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个范式已经过时了。讲到它是假问题,起于1989年何兆武对于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讨论,他首先提出来这是个假问题。当时不少人是接受这个主张的,而且从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联系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但并没有人好好地写文章讨论。
一直到2005年才有两位学者——杨师群和曹守亮,针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到底是不是假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杨师群先比较明清城镇与欧洲中世纪城市,从王权统治与工商经济、私有产权与自由雇佣等方面,论证明清社会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所谓“萌芽”是一个不存在的虚假问题。接着又从中西方专制王权对工商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及中西方私有产权对自由雇佣劳动的影响等方面,论述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个伪问题。曹守亮则主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是假问题,他从“雇佣劳动”“城市政治斗争”“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与杨师群针锋相对地讨论,批评杨师群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终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为依据,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接着,周广庆也加入讨论,从独立的工商人口、独立的生存基地、独立的工商资本、独立的组织体系4个结构性要素来证明中国古代的工商业天生患有资本主义基因缺乏症,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根本不存在的伪命题。王学典则从史学史来讨论,回避了真假问题的二分法论争,认为即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个“假问题”,但它孕育了真学术,其真学术的含量比以前的相关讨论有过之而无不及,主张不要用“假问题”去抹杀过去学者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成果的努力。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可能是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最值得骄傲的一个研究领域,因为它把一片空白的历史补上,这个研究从无到有,完全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结果。也就是说,不要去争论它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要看这个讨论实际上了解了多少明清社会经济史,这才最重要。至于它戴什么帽子,不是在这个时代所需要做的事。说戴的帽子不对,就把整个研究否定掉,这个讲法是有问题的。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的学术分析,最重要的学者是黄宗智。1991年,他在加州大学主办的《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发表一篇讨论中国研究面临的范式危机的论文。黄宗智认为中国学术的主要模式源自马克思的古典理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均出自马克思对西欧,尤其是对英国的分析,资本主义萌芽论则是中国特殊的模式。如果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是单纯的封建社会,那么就必须肯定西方帝国主义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但这是任何爱国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西方帝国主义到来之前,中国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西方帝国主义打断了这一进程,才使中国沦为“半殖民主义”。如此,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协调了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和基于民族立场的反帝情绪。
八、新研究范式的出现
王国斌、彭慕兰与李伯重的著作出现,是这段时间的代表,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逐渐退场后的新发展。他们虽然不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范式,没有清楚地说要批判停滞论,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批判停滞论。他们提出以中西方历史作比较,西方在前近代有哪些发展,中国在前近代有哪些发展;又说过去比较中国跟西欧,由于中国地大而多元,各地发展不均衡,如果拿一个比较落后地区的案例跟欧洲最先进的英国来比,等于是拿最差的跟最强的来比,这是不合比例原则的。要比,就双方面都得拿出最强的来比;所以他们主张拿当时西方发展最典型的英国跟中国发展最先进的江南来比,才能看出来一些问题。
比较中西方历史的时候,过去总是以西方经验为准,来查看中国合不合其标准,看看从近代西方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近代性”,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这其实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人类历史发展有普世的共性,也有各地特殊的个性,不能一概而论。王国斌的《转变中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就写了从欧洲经验来研究中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三方面入手,通过在长时段之中比较中国与西欧在经济、政治、社会三个方面历史的异同,有力地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学说,也展现了中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史的总体脉络和各自特点。另外,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认为18世纪产业革命之前,中西双方的社会发展是很接近的,处在基本相近的发展水平上,也都在发展农村和城镇手工业及商品市场经济,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发生产业革命,历史才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中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此后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彭慕兰把这个中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
其实这个论点并不是彭慕兰凭空发明的。20世纪60年代末期,西方已经由门德尔斯提出一个近代经济发展的新讲法,把产业革命前的经济形态称为“Proto-Industrialization”,这个名词国内翻译为“原工业化”。其实这个翻译是有点问题的,“proto”不是“原始”,而是“初阶”;“Industrialization”也不能译成“工业化”,应该译成“产业化”,因为它包含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和工业都在内的。
这个产业化初阶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农村手工业,一个是散作制。一方面,因人口增加的压力,农村家庭发展手工业副业,以为生活补助;另一方面,城镇手工业者或商人资本家利用农村增加的人口产生的廉价劳力,将手工业原料供给农村家庭手工作坊,或预付包买农村家庭手工业产品的方式,获取农村生产的利得。产业化初阶理论所注重的西欧农村手工业及商业资本介入生产之包买制,的确与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相似,可作研究借鉴。尤其主张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有联系的论断,甚为中国学者所欣赏。因此,当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学者接触到西方传入的学说时,就发现这个“Proto-Industrialization”很可以补充马克思学说来诠释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傅衣凌首先在《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一文中提到“原始工业化”。于是不少学者提倡以“Proto-Industrialization”研究范式取代被批评而渐失势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虽然有学者质疑这个研究范式,因它过分强调农村手工业的作用,忽视城镇手工业及其与农村手工业的关系,而且其强调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有联系的论断也遭受质疑。但由于一般中国经济史研究学者对西欧经济史知识生疏,以之为借鉴的实际研究成果很少,难以成为主流研究范式。
彭慕兰的讨论其实就是顺着“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论发展来的。中国学者跟西方学者对话,应该就在这方面去做努力。李伯重就是一位肯反省和创新的学者,他主张今后中国经济史学研究要摆脱旧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以开创史学新局面。他从“Proto-Industrialization”出发,提出“早期工业化”理论来取代“Proto-Industrialization”研究范式。他要改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过分注重生产关系研究、忽略生产力研究的状况。于是提倡研究工业赖以发展的主要物质条件,比如说劳动力的供求、资源的配置、技术与资本构成等方面的问题;要开展纺织工业以外的其他手工业及其生产力的研究,而且要将城乡手工业作为一体来研究,不能够分别单独研究。李伯重提倡的“早期工业化”研究范式,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学界非常值得关注和努力的新方向。
结 语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虽已退场,但它在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已经确立:第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的有关研究,搜集了大量方志、笔记、文集、官方档案和民间文献、碑刻、契约及实地调查材料中相关史料,从无到有,填补了过去我们对明清社会经济史认知的空白。第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破除了长期盛行的“中国停滞论”,以及忽略传统中国社会内变能力,认为只有靠外力才能打破停滞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具有极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为寻求合理解释前近代的明清社会经济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在学术史上有极重大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量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都是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下完成的。
作者徐泓,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座教授,厦门大学终身讲座教授
文章来源: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634674183790461297
https://new.qq.com/rain/a/20210824A065Q700